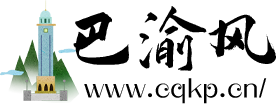
 重庆市反邪教协会主办
重庆市反邪教协会主办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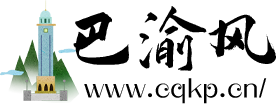
 重庆市反邪教协会主办
重庆市反邪教协会主办


近日,北京、内蒙古中部、华北北部和东部多地出现大风天气。
风,仿若隐匿于世间的精灵,无形却处处留痕。从古老的甲骨文字,到汉代精妙的气象仪器,再到现代先进的风力发电设施,古往今来,人们始终以独特的方式与风“打交道”,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。
古法观风:羽毛辨来风 乌首定风向
殷人刻甲骨以录四方风名,周人以“伣”(qiàn)测风向,此乃华夏测风之始。殷商时期,先民在风竿系上鸟羽制成的“候风羽”,通过羽毛飘动方向判断来风。
汉代,测风工具迎来了第一次革新——汉武帝建章宫顶的铜凤凰“下有转枢,向风若翔”,其随风转动的特性比西方候风鸡早千年问世。东汉张衡铸“相风铜乌”,南北朝改良为轻便木乌,“遇风乃动,乌首所指即为风向”,这项发明被广泛用于宫廷、车船与边防。
到了唐代,李淳风在《乙巳占》中完成划时代突破,将风向细分为24个方位,更以“动叶、鸣条、折枝、坠物”等自然现象为标准,创立“十级风力”体系。这较欧洲蒲福风级早1100余年,在世界测风史上前无古人。
宋元时期,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详录龙卷风“插天如羊角”的形态与灾害,成为我国首份龙卷风科学报告;东南季风因助商船返航得名“舶趠(chuō)风”,体现古人对季风规律的掌握。明清西方气象学传入后,传统智慧与近代科学结合,推动理论向“气压”“大气环流”等现代概念转变。
今朝驭风:风机锁绿电 网格测风云
如今,人们与风的“交流”不只停留在观测阶段,更延伸至对其的“驾驭”。面对化石燃料导致的环境难题,风力发电成为减排温室气体、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,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。
“风电场选址的核心门槛为年平均风速5米/秒、年等效满发小时超2000小时。”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中心高级工程师贾蓓西强调,开发风能需综合考量盛行风稳定性、电网接入条件等多重因素。风机叶轮的转动暗藏精密法则:3米/秒启动,12米/秒达额定功率,一旦风速超过25米/秒(10级风),保护系统立即触发停机,设计风速通常不超过50米/秒,极端天气易超过设备极限。
由此可见,大自然之不可抗力。但即便挑战重重,人类“驭风绘绿景”的决心不改。为精准捕捉风能资源,我国气象部门构建起“空—天—地”一体化监测网络——1公里分辨率资源普查系统整合数据生成4套精细化数据集,风光资源预报体系覆盖0小时至14天,为电网调度提供决策支撑。如今,古人的“占风旗”已变成实时数据流,苏轼笔下的“舶趠风”也化作风机动力。
未来风劫:气候促风频 飓力破新高
随着全球变暖加剧,风正变得更剧烈、频繁。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孔锋指出,全球变暖通过温度差异驱动、强对流激发、气候系统扰动三大机制,增加大风频率与强度。
首先,不同区域升温速度不均,导致高低纬度间、海陆间温差扩大,气压梯度增强,促使空气流动加速。例如北极加速升温使极地涡旋减弱,冷空气频繁南下,导致我国北方冬季大风频发;北方地表气温偏高,与南下的冷空气形成更大温差,进一步强化气压梯度与风力。
其次,大气能量与水汽随升温增加,大气不稳定度提升,强对流活动更易触发雷暴大风、飑(biāo)线等极端风事件。
再次,全球变暖干扰厄尔尼诺与拉尼娜等气候现象,改变大气环流格局。另外,北方植被退化降低地表摩擦力,北极海冰融化重塑环流模式,共同助推风势增强。数据显示,近地面平均风速虽呈下降趋势,但极端大风事件明显增多。
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韩荣青认为,海洋变暖为超强台风提供“能量库”。热带气旋依赖海温与水汽蓄能,全球变暖使海表温度升高,直接提升台风强度上限,部分热带气旋风速可在24小时内暴增。研究表明,海温每升1℃,台风潜在强度增强约5%,未来极端台风或更频繁突破历史极值。
从候风羽到风机矩阵,人类不断探寻与风的相处之道。面对气候变局引发的风暴,唯有共同担起减碳责任、守护自然规律,才能在与风的互动中锚定希望。
(作者于桐系中国气象报社记者)
 相关阅读
相关阅读
 热点文章
热点文章